借鏡智利:對「另一種未來」的思考
- 觸外

- 2022年1月28日
- 讀畢需時 11 分鐘
吳建亨(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無調性的未來?[註1]
近兩年台灣國際地位大幅提升與國內半導體產業脫不了關係。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2019年11月舉辦的台積電運動會記者會上便指出,台灣半導體技術的優勢將成為「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隨後全球產業受疫情影響,加上美中新冷戰格局,張忠謀這番評論除了一針見血,也略顯含蓄。舉例來說,2021年05月台灣疫情爆發後,疫苗短缺導致人心惶惶,「晶片換疫苗」的傳聞四起。日本與美國在疫情嚴峻時捐助疫苗之舉檯面上雖是對311震災捐款與口罩外交的回報,但從全球疫情的嚴重性與各國對疫苗需求的急迫性觀之,美日兩國當時對台灣的捐贈數量實不合常理也不符比例原則,不難看出這些看似償還人情的舉動背後與晶片地緣政治之關聯。隨後鴻海與台積電在奇貨可居的全球疫苗市場成功購買1500萬劑BNT疫苗更印證高科技跨國企業地緣政治的影響力已不遜主權國家。甚至有美國戰略專家建議,台灣應建立半導體產業自毀機制,做為未來台海戰爭中的自保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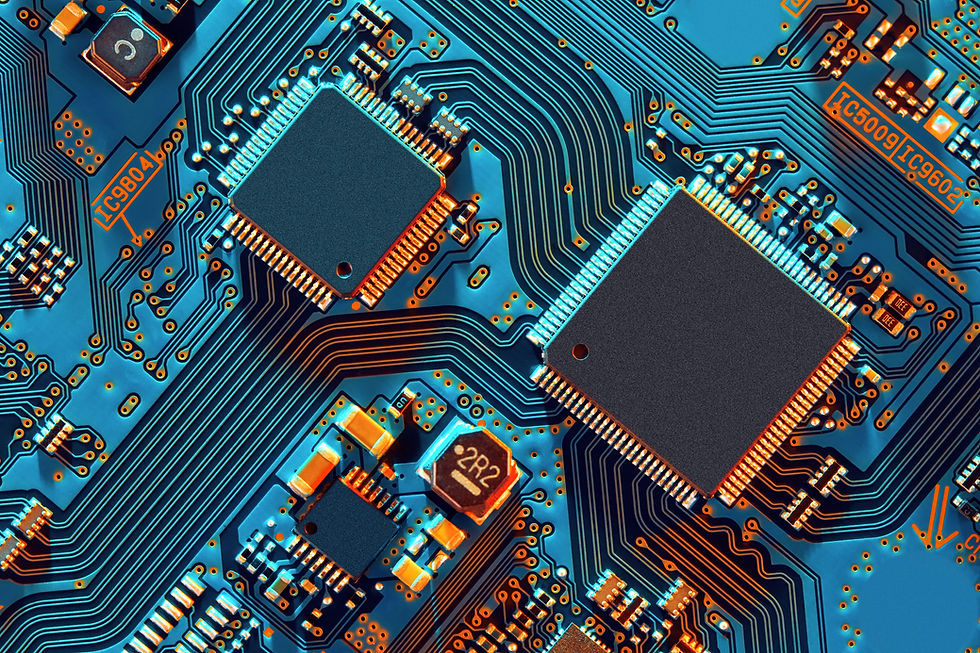
除了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外,以半導體產業為首的高科技護國群山也在疫情肆虐下撐起台灣經濟。台灣政府聲稱經濟是近二十年最好,2021年GDP成長破6%,股市也在去年狂漲23.6%,一舉衝破萬七關卡。不僅如此,高科技的蓬勃發展也帶動其它相關展業,例如晶片供應鏈中的航運產業傳出羨煞眾人的40月年終獎金,社群媒體更流傳某航海王靠這波股市操作在2021年獲利45億台幣。這些發展不僅確立台灣以科技島自居的定位,更將台灣的未來緊繫其科技的發展。因此維持各項技術的領先成為提升台灣國際地位與國際競爭力最強而有力的後盾。在此考量下,台灣不僅於2021年底前分別在台大、成大、清大、陽明交大成立四間半導體學院,更持續深化對AI人工智慧的研發,企圖憑藉軟硬體的雙管優勢讓台灣一躍成自動化世界的領航者。
然而,在此美好前景下卻藏著無法被忽視的矛盾。關於晶片、AI與自動化的論述中,我們被告知這些發展將帶來更便利的生活、更有效的管理與更長久的經濟榮景。諷刺的是,人民對生活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困頓。照理說,長期受政府扶持的科技產業所創造的經濟紅利應該分享給社會弱勢,但我們看到的卻是財富的集中與貧富差距的擴大;照理說,自動化社會應該減少勞動時數,騰出更多時間讓人民從事更多知性活動,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工時因工作與生活界線愈趨模糊而無限延長與演算法的自動化對個體自主性的侵蝕;照理說,科技為台灣帶來的國際認可與經濟榮景應令人民感到驕傲與自信,但我們看到的卻是如「躺平主義」與「父母扭蛋論」反應出的深層無力。面對這些矛盾,或許我們應該跨過數字的迷思,重新思考台灣做為科技島嶼的意義。如果科技創造更大的經濟利益,我們該問:「利益屬誰?用於何圖?」;如果科技帶來更有效的管理,我們該問:「管理的對象與其動機、目的為何?」;如果科技創造更便利的生活,我們更該問:「這樣的便利是讓我們擁有更多閒暇探索潛能,抑或限縮主體空間,讓演算法制約下的行為反射(behavioral reflex)取代個體化過程所需的批判思考(critical reflection)?」。[註2]
過去幾年我們不斷被灌輸晶片生產與AI發展至關重要,但重要的意涵為何目前似乎尚未有明確論述,彷彿其迫切性全來自某種輸不起的壓力——科技讓世界看到台灣,讓台灣不再被孤立,若不繼續維持技術的領先,台灣在未來的世界便無立足之地。然而,這種輸不起的壓力源頭不就是弱肉強食的自由市場競爭?那個未來的世界不就是當前新自由主義「最不糟糕」的世界之延續?[註3]如果台灣被世界認可的代價是進入既有的剝削體制,是被迫在美中新冷戰格局選邊站,是不斷掠奪自然資源維持生產消費的成長,是見證財富不斷增加貧富差距卻創歷史之最的矛盾,這樣的認可值得期待的嗎?在一個不公義的世界中成為前段班學生真的是我們想要的未來嗎?如果科技發展是台灣(甚至全球)的未來,或許我們不該只是執著是否能在一個已被規劃好的未來佔有一席之地,更該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樣的未來?」才是適合人類與其它物種生存的未來。如此,我們方能跳脫當下新自由主義對未來願景的限縮,想像另一種科技與社會的關係,讓台灣科技島的美稱能建立在對科技發展厚實的人文思辨基礎上,而不只是攸關半導體晶片的製程與產能。
或許有人認為上述觀點不切實際,忽略政治現實。但過去君權神授、種族歧視、性別歧視等觀點不也被認為是牢不可破的政治現實?綜觀歷史,不難發現啟蒙進程是由一連串化不可能為可能的政治實踐組成,這些政治實踐挑戰與改變的就是那些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現實」。拒絕無調性的未來非癡人說夢,事實上七零年代初期發生在智利的一場政治實驗可提供台灣借鏡參照。雖然當時的時空背景與今日大不相同,但關照智利這段歷史可讓我們了解,對未來的想像絕非如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所言:「沒有其它選項」。[註4]

賽博協同計畫(Project Cybersyn)
賽博協同計畫的起源與一封信件相關。英國控制論者比爾(Stafford Beer)在1971年7月突然收到一封來自智利的信。信件作者佛羅雷斯(Fernando Flores)當時在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左派聯合政府負責企業國有化與相關的生產事務。佛羅雷斯早期已熟悉比爾的管理控制論(management cybernetics),此時他佔據一個具影響力的位置,於是寫信詢問比爾是否有興趣將管理控制論運用在國家層級的極度複雜系統上。
比爾很快允諾,因為他在控制論與智利的社會主義革命間看到概念的共通性。簡單來說,控制論透過反饋(feedback)或遞歸(recursion)的機制,讓整個系統(包括內部各組成部分)與外在關聯環境維持動態生成的關係,使系統成為一個能因應外在環境變化自我修正的可生存自我組織(a viable self-organization)。在這個可生存自我組織中,最終的理想是建構一個去中心化系統,維持整體穩態(homeostasis)的同時也確保內部各階層的自主性。阿葉德的社會主義革命有著相同的理想,他想跳脫當時美蘇冷戰地緣政治的框架,走一條與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道路,以和平的方式在憲政體制內為智利社會帶來去中心化的結構性改變。換句話說,比爾的控制論與阿葉德的社會主義革命兩者對如何建構一個同時可以保持組織穩定又不犧牲個體自主的系統之問題深感興趣。這邊我看到政治與科技的初步結合,如果國有化是阿葉德政府朝向社會主義政治實驗的第一步,邀請比爾主持賽博協同計畫就是將科技納入這場政治的實驗。
本文無法詳述賽博協同計畫完整的發展史,我僅列舉一例說明智利如何在科技系統的建構中融入追求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念,透過工人參與工廠建模的方式,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鑲嵌入賽博協同計畫,讓科技發展的目的不只促進經濟生產的效能,也能在過程中實現工人賦權的目標。[註5]
以管理控制論為基礎的賽博協同計畫被賦予的任務是在企業國有化後維持大幅擴張的公部門之運作與工業生產的產能,需要建立一個橫向與縱向溝通的網路系統,讓政府能夠依照不斷更新的數據做更動態的決定。智利在一九七零年代初期的科技資源相當貧乏,全國只有四台大型電腦。如此貧乏的科技環境常遭受西方專家質疑智利當時不可能有能力透過科技進行組織改造的任務,但比爾認為控制論是一門關於「組織效能的科學」(“the science of effective organization”),打造有效的科技系統不必然需要最先進的科技,好的設計與規劃,搭配領導團隊對科技的理解,加上其它客觀條件配合即可能成功。比爾利用當時智利擁有的電傳網路做為賽博協同計畫信息傳輸之骨幹,其後更進一步政治化此科技系統,在程式設計的層次注入社會主義價值觀,深化科技發展與政治理念兩者相互形構的關係,形成一個同時能夠實時調節與計畫未來的可生存系統。下列僅以賽博協同計畫中增加工人參與度為例,說明科技系統如何成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載體的同時也賦予其內涵,避免後者凝固成教條式指導方針。
一般我們認為增加工人參與度指的是增加工人代表的數量,讓更多工人代表加入治理委員會。但比爾認為,這樣的理解仍在代議政治(representative politics)框架下想像工人參與,是一種對社會主義教條式的理解,僅增加工人往上爬升進入治理委員會數量,沒有改變結構性的問題,因為那些成為代表的工人通常會形成與底層工人脫鉤的小團體,扮演起過去管理階層的角色。這種情況下,工人參與度的增加只是照本宣科地執行社會主義的明文規範,並沒有實質改變工人與工作的關係。
比爾提倡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工人不再被動地使用或執行一個已經被其他專家設計好的工具,而是實際為工廠建構模型並讓他們的知識進入軟體的參數設定。比爾認為,將社會主義鑲嵌入科技系統僅提供一個大方針,但這個方針非已然成形、封閉且死板的教條式規範,其確切型態為何取決於底層自主性的動態展演。換句話說,社會主義與科技系統的關係不能以線性指揮鏈理解,工人參與度提升是社會主義的大方向,但目標具體實現的模式不是在既定的框架內進行——例如讓更多底層工人往上爬升為委員會代表——而是透過權力下放的方式,讓工人長期累積的知識成為軟體模型設定的參數。參與式設計仍需某種再現(representation)機制,畢竟社會主義價值觀即為一種對世界的再現,但其實質內涵非依循既有教條由上而下規範;而是由下而上(例如納入工人的知識)依情境動態調整逐漸成形。
科技系統設計的問題無法辦法避免價值觀介入,因此重點不在力求絕對的客觀,而是讓具包容性且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進入程式設計中。[註6]這也是比爾想做的事情,讓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進入賽博協同計畫,其中一個做法就是讓程式設計以工人的知識為基礎,而不是讓工人被動學習一套專家設計好的東西,也不是單純地增加工人代表數量。比爾的結論是:如果讓工人參與科技的使用與設計,這樣就能形成一種新的工人賦權。
智利的911事件:被壓抑的過去與被棄絕的未來
如果智利是孕育新自由主義的搖籃,她也將成為其墳場。
——博里奇(Gabriel Boric),智利總統當選人[註7]
1973年9月11日,皮諾契特(Augusto Pinochet)將軍在美國中情局協助下發動軍事政變,總統阿葉德飲彈自盡,賽博協同計畫也戛然而止。皮諾契特主政後由芝加哥大學教授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擔任經濟顧問,相關內閣成員也由傅利曼門下一群被稱為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的信徒組成。這些人在智利開啟新自由主義的實驗,進而擴散全球,成為今日主宰世界的霸權。[註8]根據波坦斯基(Luc Boltanski)與希亞佩洛(Eve Chiapello)的說法,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會吸納所處時代的創新理論並動員這些概念做為自我蛻變與正當化的手段。[註9]源於美國四零年代的控制論到了七零年代中後期被全球資本主義吸納,這段資本發展軌跡也使控制論的定位變得更加複雜;智利七零年代歷史見證了控制論具體實踐的兩個極端,讓我們看到理論的藥/毒雙重性:一方面,控制論去中心化的組織思維被用來建構賽博協同計畫,實現阿葉德對智利模式社會主義的願景;另一方面,這種去中心化的思維也被新自由主義動員成一種新型態的控制技術,透過控制論的反饋機制,計算環境變數並進行相對應演化以維持系統之穩態,將本體層次的未知調控成知識層次的或然率,使「未來」時間範疇不再是不可預測的基進偶然(radical contingency)。
至此,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控制論的實踐在智利未竟全功,日後卻成就新自由主義全球霸權?難道控制論必然導向無調性的未來嗎?若無此必然性,我們是否可以對控制論做另一番想像,藉此開創不同格局的未來呢?本文冀望透過對智利七零年代這段歷史的簡述鬆動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必然性之論述,為未來勾勒另一種可能,也盼台灣對科技的追求能有更全面的考量,而非單純想在既有秩序內佔有一席之地。
註釋
[1] 無調性(atonality)原為一種音樂表現形式,此處用法依循巴迪烏(Alain Badiou)賦予該詞的反動意涵,泛指看似民主的多重流變狀態,其中缺乏任何規約面向,因此無需評量(evaluation)與決定(decision)等賦予未來方針或目標的動作。相關討論見Logics of Worlds, 420-422。
[2] 康德(Immanuel Kant)在〈答「何謂啟蒙」?〉(“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對未啟蒙狀態的「不成熟」(immaturity)如此描述:『假如我有一本書充當我的理解,一個牧師充當我的良知,一個醫生為我決定飲食,諸如此類,我便不需自己勞心費神』。今日的演算法將上述各種權威角色融合為一,透過友善可藹的虛擬化身(avatar),以「建議」(recommendation)的方式調節使用者的行為模式,如購物的選擇、閱讀的書籍、投票的傾象等等,讓使用者不需為任何決定勞心費神。
[3] 上個世紀一些以解放為名的革命運動希望開創烏托邦的新世界,但帶來的卻是極權主義與人道危機,這段不堪的革命歷史如今成為資本主義最強而有力的辯護。那些為既有體制辯護的人士承認,現今資本主義體制內部的確有諸多矛盾和問題(如貧富差距),但他們強調,即便如此也總比上個世紀那些獨裁屠夫濫殺千萬人好上許多。換句話說,今日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想像與開創更公平正義的世界變成避免災難的發生。也因如此,忍受「最不糟糕」(the least bad)的選項(如新自由主義的控制社會)總比因追求烏托邦理想複製過往人道災難好上許多。資本主義的必然性在八零年代後被自然化成根深蒂固的信仰,因為缺乏其他選項,所以「最不糟糕」的選項順理成章地被轉譯成唯一也最好的選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與齊傑克(Slavoj Žižek)常被引用的一句話也須在此脈絡理解:在好萊塢電影中,『想像世界的毀滅遠比想像資本主義的終結更容易』(“It is easier to imagine the end of the world than to imagine the end of capitalism”)。
[4] 『沒有其他選項』(There Is No Alternative, or TINA)是前英國首相柴契爾推行的口號,認為除了市場經濟外別無其他選擇。
[5] 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6] 近年來不同脈絡也有類似比爾觀點的討論。例如有學者指出,谷歌(Google)或臉書(Facebook)的演算法隱藏許多深層偏見,不只是某些刻意的設定(如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刻意過濾關於川普相關訊息),而是在程式設計的層次夾帶的深層偏見。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資訊研發人員有幾乎相同的背景(特定性別與特定學術養成的經歷等),這些人在程式設計上便會不自覺地將同溫層的偏見灌注設計中。如韋伯(Amy Webb)在《AI未來賽局》(The Big Nine)指出:『人工智慧的未來正由一小群人打造,這個團體相對封閉,人員的想法也高度相似。再次強調,我相信這些人的本意良善,但要是這些封閉的團體不斷密切合作,假以時日,即便他們不是存心為之,他們的偏見與短視很容易成為新的信念系統以及大家能接受的行為』。因此有些人開始提議,要求這些未來工程師不能只修習專業課程,需有一定比例必修學分分配給性別、種族、階級等議題的相關學習,目的是避免具壓迫性與短視近利的意識形態不自覺地進入程式設計中。
[7] 智利去(2021)年十二月經歷了近三十年來最分歧的總統大選。被視為阿葉德繼承人的左派候選人博里奇在第二輪投票後來居上,以三十五歲的年紀成為智利史上最年輕的總統當選人。博里奇誓言打擊貧富差距與對抗新自由主義,勝選後的二十四小時內更有支持者建議博里奇重啟賽博協同計畫。
[8] 相關討論見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 Chap. 3 “States of Shock: The Bloody Birth of the Counterrevolution”。
[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104.
吳建亨
現任清華大學外語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包含歐陸哲學、後殖民研究、後人類研究與台灣研究,專注解放與抵抗衍生出的政治與倫理問題。




留言